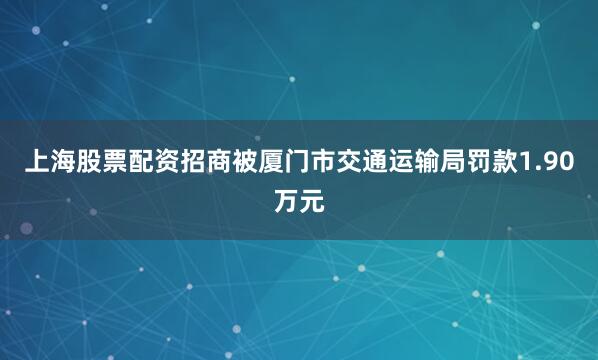【1953年腊月二十清晨】“绍辉,我在村口等你半天了!”三六阿公扯着嗓子,大半个瓦子坪的人都听见了。冷风里,这声招呼带着乡野特有的爽朗,也拉开了彭绍辉离家二十六年后的首次探亲。
车子刚停稳,警卫员跳下车,礼貌却生疏地挡住人群。乡亲们并不介意,他们记得当年的看牛娃,如今已是一位独臂上将。彭绍辉推开车门,立刻被簇拥的乡音包围,他先是抬手敬礼,然后一句土话脱口而出:“各位噶子,日子还过得打劲不?”一句话惹得众人乐呵,压在心头的拘谨瞬间散去。

他沿着青石板路一路握手,目光却总忍不住望向那片油茶林——童年赶牛时常钻进去偷懒的地方。队伍走到老屋门口,他忽然停住脚步:“今天别忙张罗酒席,我只想问一句,大家能不能顿顿吃饱?”人群里有人喊“能”,有人点头,有人低头抹泪,场面热烈又质朴。彭绍辉笑得像个孩子,衣袖空荡荡地随动作轻轻晃动。
午后,三六阿公好不容易挤到院门,却被警卫拦下。老汉火气蹿上来:“彭绍辉,我跟他挨屁股长大的,他回来连面都见不得?”彭绍辉闻声而出,冲过去拽住老友的手,两人掌心摩挲,粗糙、温暖,一点不比当年少。三六阿公一开口便是一句调侃:“你这官咋当的?连兄弟都认不进门?”彭绍辉哈哈大笑:“怪我怪我,小兵当糊涂了!”一句“兵”而非“将”,把昔日伙伴的隔膜拆了个干干净净。
夜幕降临,瓦子坪老屋灯火通明。彭绍辉端着自家土烧酒,同学、宗亲、学堂先生轮番落座。话题从早年挑粪、到长征途中断臂,再到抗日、解放、抗美援朝,一茬接一茬。有人问伤臂,他轻描淡写:“在长征过乌蒙山时挨了弹片,命捡回来了,赚大了!”满屋哄笑,笑里却带着敬意。席间他反复嘱咐村支书:“分田定产以后,可别吃老本,水利得跟上。”谁都能听出,他来不是作秀,是真想把战场经验换成家乡发展的点子。

三天倏忽而过。临别那天,他把乡亲的手一一握紧:“下回回来,咱们看合作社的稻谷仓能装满几仓。”车子转出村口时,他回头望,霜白的山头像极了部队里的号角声。
十多年眨眼即逝。1965年“五一”后,他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再次回到杨林。没有鞭炮,没有横幅,先听民兵汇报,再钻进机耕道勘水势。他把新式步枪、手榴弹样品往桌上一放:“要训练,就按正规军的章法来。”乡党委书记在一旁惊叹,乡亲们第一次发现——作战之外,他的专业是动员千百万普通人保卫家园。
1969年国庆,北京。天安门城楼上,毛主席握住那只独臂:“你是瓦子坪的看牛娃。”一句话让身旁的记者侧目。这一幕被拍成照片,传到韶山,老人们感慨:咱村出去的仔子硬气。

1971年夏,他在韶山宾馆设家宴,把嫂嫂汤氏、侄子侄女一口气都接来。给嫂嫂布菜时,他忽然愧疚:“当年走得急,留你含辛茹苦。”得知嫂嫂手头拮据,他马上请韶山当地负责同志“想个法子,让老人家安心”。几年里,汤氏每逢换季都能收到慰问金和药费,老人逢人就说“小叔子有良心”。
1973年,杨林乡党委写信求助交通难题,他自掏腰包五百多元,托部队维修厂寻来一辆二手“解放牌”,车头还刷着“支援家乡”四个大字。那一年粮食喜获丰收,新车在稻谷堆里穿梭,孩子们追着它叫“绍辉号”。
1975年,近古稀的他带妻儿回村扫墓。父亲坟前,他沉默了很久,只作三个深鞠躬。大雨封山,本想上山祭母,只得作罢。转身见到当年那三间茅屋,他对孩子们说:“从前,这屋漏雨漏到被窝里,现在谁家再漏,找大队长,一准给修。”那天傍晚,他发低烧,被迫提前返程。临走仍摇下车窗:“三年后我再回来!”

时间却不给机会。1978年春,他的身体终于扛不住多次战伤与劳累,病情恶化。当他对护士嘀咕“家乡油茶花该开了”时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4月25日,他静静地合上眼睛,再也没走出病房。
瓦子坪的老友说,将军走得安详,因为故乡不再贫困;军中特意为他停枪致哀,因为战友记得独臂挥指的身影;史料里留下简短评语“对党忠诚,胸怀人民”,却难以写出当年那一句“你这官咋当的”里的兄弟情味。今天再提起彭绍辉,乡亲们更爱用一句土话:“人硬、心软、没忘根。”将军的故事,也就活在这句话里,活在那条从老屋通向外面世界的红土路上。
辉煌配资-辉煌配资官网-网络配资炒股-股票在线配资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